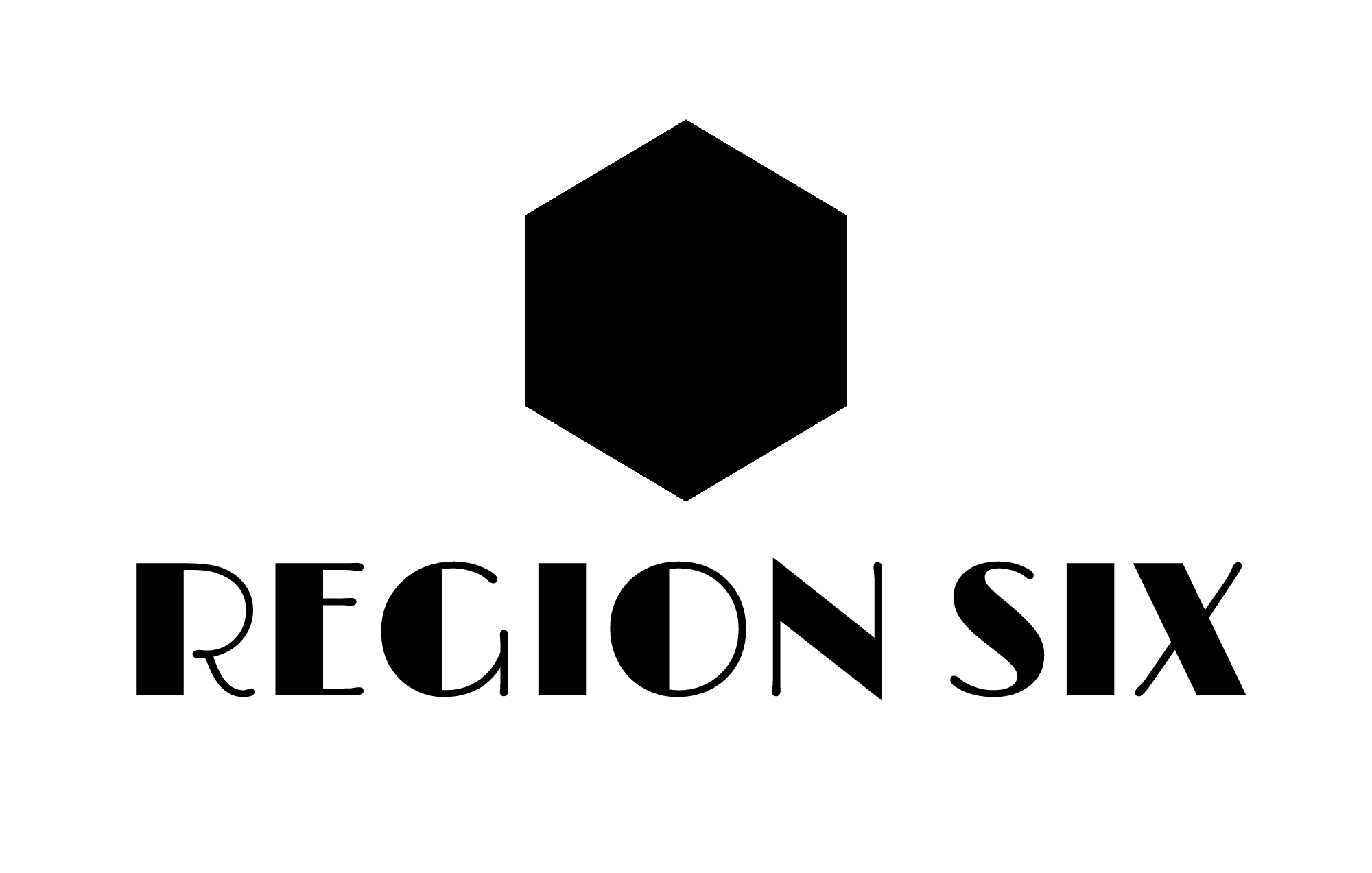2017 年 11 月 27 日
Antinatalism 哲学家大卫-贝纳特(David Benatar)认为,如果没有人再生孩子会是更理想的。
大卫-贝纳塔(David Benetar)可能是世界上最悲观的哲学家。作为一个 "antinatalist"(反出生主义者),他认为生活是如此糟糕,如此痛苦,以至于人类应该出于同情心而停止生育。「虽然许多好心人不遗余力地让他们的孩子免受痛苦,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种(也是唯一)能保证他们的孩子免遭痛苦的方式就是首先不要让它们来到这个世上」,他在 2006 年的一本名为《宁可从未存在过:出生带来的伤害》(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的书中这么写道。在贝纳塔看来,繁殖在本质上是残酷且不负责任的——不仅是因为可怕的命运可能降临到任何人身上,而且还因为生命本身 「被邪恶(badness)所渗透」。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如果有感知的生命完全消失,世界将是一个更好的地方。
作为一部学术哲学著作,《宁可从未存在过》获得了异常广泛的受众。它在 GoodReads 上有 3.9 颗星,一位评论者称其为「相信生育是合理的人的必读之书」。几年前,《真探》背后的编剧尼克·皮佐拉托 (Nic Pizzolatto)读了这本书,并让马修·麦康纳 (Matthew McConaughey)的角色拉斯特·科尔 (Rust Cohle)塑造成了一个虚无主义的 antinatalist。 (「我认为人类意识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悲剧性失误,」Cohle 说。)当 Pizzolatto 向媒体提及这本书时,Benatar 认为自己的观点比 Cohle 的更深思熟虑、更人性化,他从原本避世的生活中走出,在采访中澄清了自己的观点。现在,他出版了《人类困境:人生最大问题的坦诚指南》(The Human Predicament: A Candid Guide to Life's Biggest Questions),这是他对 antinatalism 思想的提炼、扩展和语境化。这本书以 T.S 艾略特(T.S Eliot)的「四个四重奏」的题词开头——「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并承诺为诸如「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吗?」和「如果我们可以长生不老?」等问题提供「严酷」的答案。
贝纳塔于 1966 年出生于南非。他是开普敦大学哲学系主任,也是该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是由他的父亲,全球健康专家所罗门-贝纳塔(Solomon Benatar)创立的。贝纳塔将 《宁可从未存在过》「献给我的父母,尽管是他们使我存在」)。除了这些仅有的简介,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很少。互联网上没有贝纳塔的照片;YouTube 上关于他的讲座视频只有 PowerPoint 幻灯片。有一个名为「大卫-贝纳塔长什么样?」的视频,放大了一张从演讲厅后面拍摄的颗粒状照片,直到一个标有「David Benatar」的箭头出现,指着一个戴着棒球帽的抽象的、像素化的头部。
在读完《人类困境》后,我写信给贝纳塔,询问我们是否可以见面。他欣然同意,然后,在阅读了我的其他几篇作品后,又写了一份说明:「我看到你的目标是除了描绘他或她的工作之外,也描绘采访者本身,」他写道:
一个与我相关的事实是,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如果我被写成我在其他采访中看到的那种细节,我会感到十分窘迫。因此,我将拒绝回答我认为过于私人的问题。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采访,我完全理解。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认同我这一要求的情况下进行采访,我将会很高兴。
毋庸置疑,贝纳塔天生是个内向的人。但他的匿名还有一个目的:防止读者对他进行心理分析,把他的观点归结为抑郁症、精神创伤或别的与他性格有关的方面。他希望他的论点本身就能得到正视。「有时人们会问,『你有孩子吗?』」,他后来告诉我。(他说话很冷静平稳,带着南非口音。)「然后我说,「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个虚伪的人——但我的论点仍然可能是正确的。」当他告诉我,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 antinatalist 的观点时,我问他有多年轻。「当我还是个孩子」他说,停顿了一下。他有些不自在地笑了。这正是他不愿意回答的那种私人问题。
贝纳塔和我在世贸中心见面,那里是《纽|约|客》的办公室。他矮而瘦,有一张小巧的脸,他穿着整齐的长裤和一件淡紫色毛衣;从他的棒球帽我认出了他。在大楼的第六十四层,我们在一对毛绒椅子上落座,椅子靠近窗户,可以看到曼哈顿的全景:左边是哈德逊河,右边是东河,远处是中城的摩天大楼。
社会科学家经常询问人们的幸福水平。一项典型的调查要求受访者在 1(「对你来说最糟糕的生活」)到 10(「对你来说最好的生活」)的范围内评价他们的生活;根据《2017 年世界幸福报告》,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间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平均将他们的生活评为 6.99,比加拿大人的生活(7.32)更不幸福,比苏丹的公民(4.14)更幸福。另一项调查显示,「综合考虑所有事情,你认为你是(一)非常幸福,(二)相当幸福,(三)不是很幸福或(四)完全不幸福?」 近年来,在印度、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呈上升趋势。1998 年,93%的美国人声称自己非常或相当快乐。到 2014 年,在大衰退之后,这个数字已经下降 ,但只是略微下降到了百分之九十一。
简而言之,人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贝纳塔则认为他们错了。他在《人类困境》中写道:「和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人类的生活质量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他提供了一份程度递增的困境清单,旨在证明即使是幸福的人的生活也比他们想象的要糟糕。他写道,我们几乎总是饥饿或口渴;当我们不饿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洗手间。我们经常经历着「温度不适」——我们要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或者疲倦、或者无法入睡。我们遭受瘙痒、过敏和感冒、痛经或潮热之苦。生活是一个「受挫和惹恼」接踵而至的过程——在交通中等待、排队、填写表格。被迫工作,我们经常发现工作令自己身心俱疲;甚至「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也可能有仍然没得到满足的事业憧憬」。许多孤独的人始终单身着,而那些结婚的人则争吵、离婚。「人们想变得、看上去、感觉更年轻,但他们却不停地衰老着」: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很高的希望,而这些希望往往会受挫,比如说,孩子们在某些方面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当我们身边的人受苦时,我们无法熟视无睹。当他们去世时,我们也陷入绝望。
对于这样的观察,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如果生活如此糟糕,你为什么不自杀?」贝纳塔用了四十三页的篇幅来证明,死亡只会加剧我们的问题。「生命是糟糕的,但死亡也是糟糕的,」他总结道。「当然,生命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糟糕的。死亡也不是在每个方面都是糟糕的。然而,在关键方面,生命和死亡都是可怕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性」的夹钳——紧紧夹住我们,迫使我们陷入困境。他认为,宁可首先不要进入这种困境。人们有时会问人生是否值得活。贝纳塔认为,最好是问一些次问题:生命是否值得继续?(是的,因为死亡是坏事。)生命值得开始吗?(不。)
贝纳塔远不是唯一的 antinatalist。莎拉-佩里(Sarah Perry)的《每个摇篮都是坟墓》(Every Cradle Is a Grave)和托马斯-利戈蒂(Thomas Ligotti)的《反对|人类的阴谋》(The Conspiracy Against the Human Race)等书也培养了一批读者。有许多「misanthropic anti-natalists」(反|人类的反出生主义者):例如,「人类自愿灭|绝|运|动 」有成千上万的成员,他们认为,出于环境原因,人类应该停止存在。对于 misanthropic anti-natalists 来说,问题不在于生命,而在于我们。相比之下,贝纳塔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 anti-natalist」。他的想法与研究意识和人工智能的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Thomas Metzinger)的想法相似;梅青格支持数字 antinatalism (digital antinatalism),认为创造有人工意识的计算机程序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会增加世界上的痛苦数量。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人类。
就像一个对反击了如指掌的拳击手,贝纳塔已经预见到了一系列的反对意见。许多人认为,生活中最棒的体验——爱、美、发现等等——弥补了糟糕的体验。对此,贝纳塔回答说,痛苦比快乐程度更深。疼痛持续的时间更长:「有一种东西叫慢性疼痛,但没有一种东西叫慢性快乐,」他说。痛苦也更有力量:你愿意用五分钟可以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痛苦换取五分钟最大限度的快乐吗?此外,从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来说,错过好的经历并不像拥有坏的经历那样糟糕。「对于一个存在的人,坏事的存在是坏的,好事的存在是好的,」贝纳塔解释说。「但是,将其与此人从未存在的情况相比较——那么,没有坏事是好的,但没有好事也不是坏的,因为没有人会被剥夺这些好事。」他继续说,这种不对称性「完全对存在不利」,因为它表明「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苦难都可以结束,而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代价。」
有些人认为,只谈论痛苦和快乐完全没说到点子上:即使生活不美好,它也是有意义的。贝纳塔回答说,事实上,人生在宇宙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存在于一个冷漠的宇宙中,甚至可能是一个(冷漠的)「多元宇宙」,并受制于各种盲目且漫无目的的自然力量。在没有宇宙意义的情况下,只剩下「地球层面」的意义——而且,他写道,「认为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个体可以互相帮助的这种说法,显得像是循环论证。」贝纳塔也拒绝痛苦和挣扎本身可以为生命赋予意义的说法。「我不相信痛苦会带来意义,」贝纳塔说。「我认为人们之所以试图在苦难中找到意义,是因为不那么做的话,苦难是如此毫无必要和难以忍受。」他说,确实,「曼德拉通过他对苦难的回应而产生了意义,但这并不能作为他所经历一切的理由。」
我问贝纳塔,为什么「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足以回应对他的论点。他告诉我,即使未来可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也无法让现在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合理化;无论如何,一个大幅改善世界是不可能的。「它永远不会发生。(人们)似乎从来都不吸取教训。似乎从来都不吸取教训。他说:「也许有个别的人会,但你仍然能看到你周遭的疯狂。「你可以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难道看不出你正在犯人类以前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吗?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但这并没有发生。」归根结底,他说,「不愉快和痛苦深深地写进了有感知的生命结构中,无法被消除。」他的声音越来越急切;他的眼里含着泪。「我们被要求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东西。人和其他生命都必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而且他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是不可接受的。」通常在这种对话中,我会喃喃地说一些宽慰的话。但这次,我无言以对。
贝纳塔选择了一家素食餐厅作为午餐地点,我们开始沿着哈德逊河步行前往。在维西街的尽头,我们经过了爱尔兰大饥荒的纪念馆——一片在 2001 年从爱尔兰转移过来的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用以纪念该国大饥荒中的数百万死者。在贝纳塔的建议下,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来浏览和阅读入口处展示的历史引文。饥荒持续了七年;回忆起它,一个人写道:「它在我的记忆中像是一个悲伤的漫漫长夜。」
天气有些炎热。在 Battery Park,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在草地上野餐。一群同事在打乒乓球。在水边,情侣们手牵着手散步。路上有跑步的人——没穿衣服胸肌健壮的男人,穿着时尚运动装备的女人。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信念和你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我问道。「我可不反对人们找乐子,也不否认生活中有美好的事物,」贝纳塔说道,笑了起来。我瞥了一眼,发现他已经把毛衣脱去,挽起了衬衫袖子。他的帽子似乎没被动过。我们走到了一个地点:八个星期后,一个 29 岁的男人在这里用一辆面包车杀死了八个人,伤了另外十一个人。
像其他人一样,贝纳塔也意识到他的观点令人困扰;因此,他对分享它们感到矛盾。他不会走进教堂,大步走到讲台上,宣布上帝不存在。同样,他也不愿意成为 antinatalism 的大使。他说,生活已经存在够多的不幸的了。他安慰自己,由于他的书是哲学性和学术性的,只有那些主动寻求它们的人才会阅读。他听到一些读者表达感激,说他们发现自己隐秘的思想得到了表达。一个有几个孩子的男子读了《宁可从未存在过》,然后告诉贝纳塔,他认为生下他们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遭受着可怕的精神和身体折磨的人写信说,他们希望自己从未存在过。他还听到与他观点相同的人说,他们因这些观点而郁郁寡欢。「我对这样的人感到十分悲伤,」他温和地说。「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准确的,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问贝纳塔,他是否曾经觉得自己的思想难以承受。他不自在地笑了笑——又是一个私人问题,然后说,「写作有帮助。」
他不认为 antinatalism 会被广泛接受。「它违背了太多的生物驱动力」。不过,对他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希望的来源。「面对这整个世界的疯狂——你或我能对此做什么?」在我们散步时,他说。「但每对夫妇,或每个人,都可以决定不生孩子。这就避免了大量的痛苦,这都是好事。」当朋友们有了孩子,他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辞。「我很纠结,」他说。生孩子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孩子将发现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乐观的态度使生活更容易承受。」 几年前,当一位哲学家朋友告诉他她怀孕了,他的反应很平淡。拜托,她坚持说,你要为我高兴呀。贝纳塔询问了他的良心,然后说:「我感到高兴,为你。 」
午餐时,我们坐在一个小女孩和她母亲的旁边。这个女孩大约八岁,穿着裙子,拿着一本书。「你想把这些带回家吗?」她的母亲指着一些薯条问。「好!」女孩说。
我和贝纳塔的谈话继续进行,但我发现坐在这对母女旁边时很难谈及 antinatalism。我们在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里畅聊了我们的工作习惯。在街上,我们握了握手。贝纳塔说:「我四处走走。」他计划在去机场之前在 West Village 逛逛。我向南走,在世贸中心附近,我走进了 Oculus,这是一个巨大、阴森的商场和火车站,是在 9/11 袭击中被摧毁火车站的代替品。它有高耸的、类似脊柱的屋顶和白色大理石的「肋骨」,它一半是骨架,一半是大教堂。站在自动扶梯上,我看着一个把一只手放在外套里的女人挣扎着插入另一只手。一个胖胖的商人,耳朵里塞着耳机,从我身边擦过,他的公文包推搡到了我。当他到达底部时,他拿起那女人的外套,她将手滑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