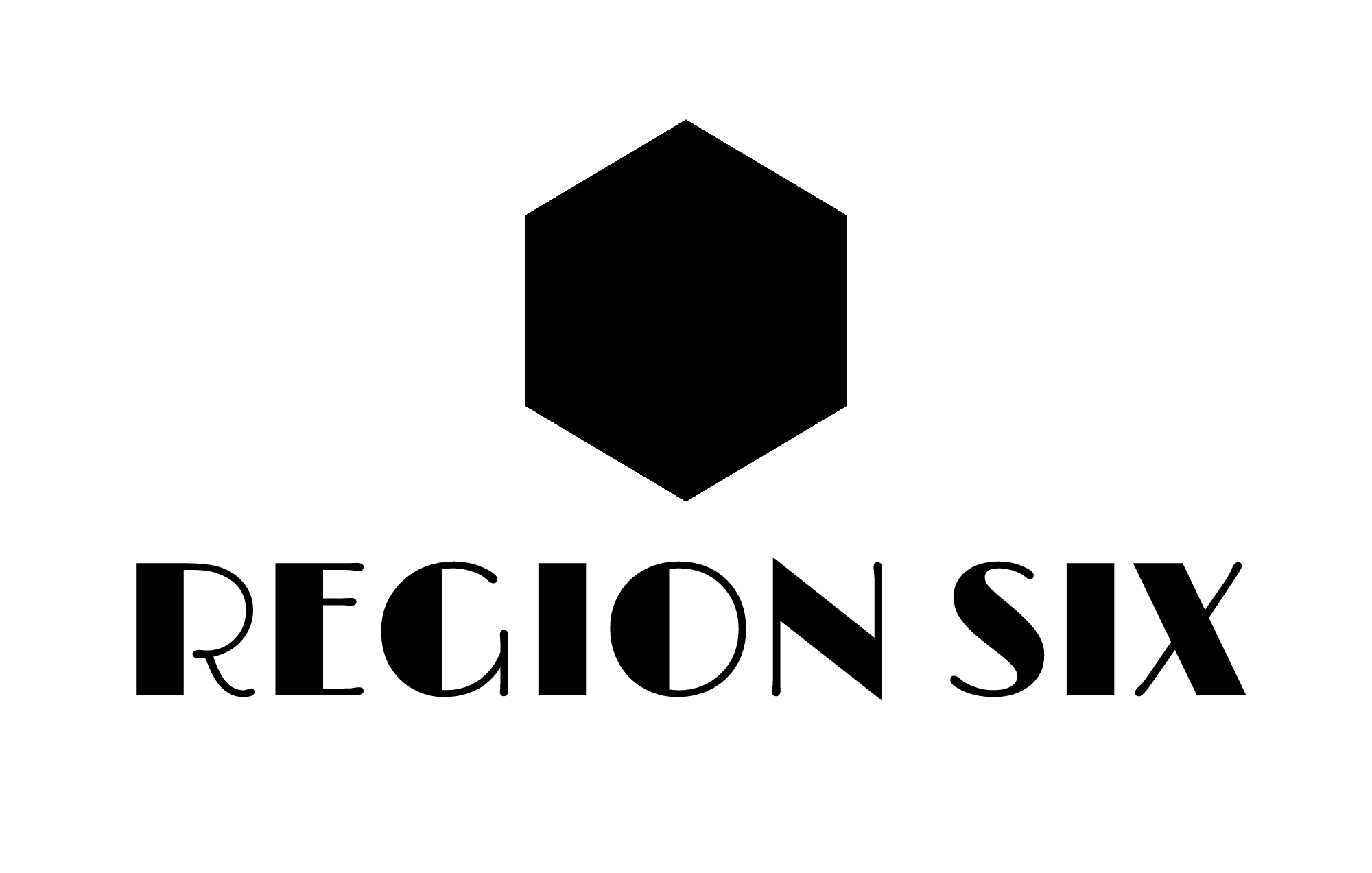译自贝老师 2020 发表的《Famine, Affluence, and Procreation: Peter Singer and Anti-Natalism Lite》,可以科学下载到。这篇论文基于辛老师超级出名的1972 年论文《饥荒、富足和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而写。后者的核心论点是: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人是生活富足的人应尽的道德责任,且不受远近距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一论点为之后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思潮奠定了基础。但推崇利他主义的的辛老师也是个 pro-natalist(生育推崇者)。他多次公开反对 anti-natalism(本人目前倾向于翻译为反出生主义)。在去年悉尼大学举办的一个在线座谈会上,当学生问及有效利他主义者是否该优先考虑领养而不是生育,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具备「利他主义」思想的家长也更可能生出具备利他主义的孩子。也就是传说中的迷因(meme)需要靠基因来传播的说法。让我十分困惑/失望。希望贝老师的这篇文章能为有同感的朋友提供新思考。欢迎对翻译作出指正。
声明:文章讨论的语境是西方发达国家。翻译本文的目的是哲学讨论,仅为参考交流所用。请读者多多关注支持国内伦理学的发展。
目录:
摘要
1 机会成本
2 生育成本
3 贫困成本
4 责任成本
结论
摘要:彼得-辛格认为,富足的人对世界上的穷人负有相当广泛的责任。他的这一论点对生育有一些重要的影响,但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承认。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首先,富人应该拒绝生育,而把那些本来用来抚养孩子的资源转给穷人。其次,穷人(也可能是以及富人)应该拒绝生育,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原本会被他们带来世间的孩子经受非常糟糕的事情。第三,富人(和其他人)有时有防止穷人生育的责任。第四,富人有时有防止穷人生育的权利。虽然这些影响可能不等于断然禁止所有生育,但它们确实大大限制了生育的可允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 anti-natalist 的。
彼得-辛格(2010a)曾简要地写过有关 anti-natalism 的观点——即我们不应该创造新的人的观点。然而,他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2010b)。对此他只提供了一些粗略的评论来支持他的结论。辛格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是值得活的,而即使现在不值得,他也是一个「足够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在一两个世纪之后我们能「创造出一个苦难远比如今更少的世界。」
虽然他没有接受 anti-natalism,他的一个表面上不相关的论点——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我们对世界上的绝对贫困者有非常广泛的责任——可能会致使那些承诺于该论点的人也接受一个不太广泛的 anti-natalism。 他所说的「绝对贫困」(或「极端贫困」,他有时用这个词来代替),是指资源匮乏到无法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的状况 [1]。
他的论证采用了以下形式 [2]:
如果我们能防止坏事发生,同时也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comparable moral importance),我们就应该(ought)防止它发生。
极端贫困是坏事。
我们可以在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情况下防止一些极端贫困的发生。
因此,我们应该防止一些极端贫困的发生。
让我们把这称为「扶贫论」(poverty relief argument)。接受这一论点的人可以对其的苛求度(demanding)持不同意见。它的苛求度有多高,将取决于我们在不作出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的情况下能够防止多少极端贫困。这是因为该结论要求我们在不作出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的情况下,防止我们能防止的一切极端贫困。彼得-辛格 [3] 本人认为,由于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的道德重要性无法与极端贫困相提并论,因此所需牺牲的范围很广的。对于他和那些同意他结论苛求度(demandingness)的人,需要承认生育不被允许的情况似乎比他们和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即使他们可能不情愿地承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生育都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好像也从未指明这一点。因此,就该论点和其结论的苛求度的解释来说,强调「扶贫论」对生育的影响是有一定价值的。
此外,其中的一些影响,包括富足的人有时有阻止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生育的道德责任,会让激进人士感到不适。鉴于这些人士最可能接受世界上的富人对世界上的穷人负有广泛责任的这一结论,正如我将论证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面临两难境地。要么他们必须接受「扶贫论」对生育的影响,要么他们必须质疑彼得-辛格的论点,或至少是质疑对其结论的苛求度更高的那些解释。
扶贫论的论点虽然由一位著名的功利主义者提出,却是专门为了绕过功利主义者和非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提出的(Singer 1993, p.199)。这样,他们便可以同意我们应该在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情况下防止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即便他们对什么是「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sacrifice of comparable moral importance)各执一词。因此,扶贫论对生育有什么影响,可能部分取决于一个人所接受的伦理理论。换句话说,该结论之于生育行为的含义在功利主义者、德性论者、美德论者和其他人眼中会有所不同。
[1] 在文章中的一处地方,他曾赞许地引用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定义:「一种以营养不良、文盲、疾病、肮脏的环境、高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为特征的生活状况,以至于低于任何人类体面生活的合理定义」(Singer, 1993, p.219)。在其他文章中他遵循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的定义:「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人类对足够的食物、水、住所、衣服、卫生设施、保健和教育的最基本需求」(Singer, 2009, p.6. )
[2] 他的论点第一次在(Singer, 1972)中得到阐述。在那之后在他不同的论证形式中该论点略有变化。本文列出的来自(Singer, 2011, p.200)
[3] 虽然我熟知(在首次提及后)只使用姓氏的学术惯例,但出于礼貌,我避开了这一惯例,倾向于使用名和姓,或头衔和姓氏。见(Benatar,2019a)。更完整的论证见:(Benatar, 2019b)。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将「anti-natalism」的标签用于(仅仅是)寻求大幅减少而不是断然反对生育的观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遵循这种想法。我们并不会将「pro-natalism」的标签只用在建议所有人将生育力最大化的观点。相反,我们会在描述旨在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时使用这个词。同理,「anti-natalism」可以用于形容减少人口的政策。因此,中国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样的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是 anti-natalist 政策。当然,我现在认识到,彼得-辛格可能接受最低限度的 anti-natalist 结论——例如,我们应该限制我们孩子的数量。在本文中,我将论证的是:他的论点,至少在其结论非常苛求时,是支持更广泛的 anti-natalist 结论的。那些不顾我所说,除了给反对所有生育的人之外,不喜欢给其他任何人贴上「anti-natalist」标签的人,只需重新表述我的结论便可。他们可以说,在我概述的以下条件下,扶贫论和对其结论的苛求度的解释意味着反对生育。
1 机会成本
首先,也许是最明显的,是彼得-辛格的论点意味着,至少在目前,相对富裕的人应该停止生育,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抚养孩子所需的资源来防止极端贫困。这种特殊的含义首次由斯图尔特-拉歇尔(Stuart Rachels)[4] 明确提出。
在发达国家,养育儿童的成本很高。评估成本的方法显然有所不同。即使没有不同,它们也只能确定一个平均或代表性的成本。一些父母显然比其他人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花费更多。然而,在第一世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到 18 岁的平均成本在 20 万到 30 万美元之间(Cornell 2011;Brown 2015;Lino et al. 2017)。支出通常也不会就此结束。十八岁以后的费用包括大学教育,可能达到数万美元,在美国私立大学的就读甚至会达到几十万美元。
通过生孩子,一个人创造了需求(和欲望),凡是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果一个人不生孩子,他就能释放出资源,并能防止大量坏事的发生。当然,许多人想生孩子。对他们来说,停止生孩子是一种牺牲,但这是一种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牺牲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确定这个牺牲到底是什么。有一种解释是,它只是放弃了拥有自己基因的后代,因为一个人仍然可以收养一个已经存在,曾不被人需要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既可以防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孩子在孤儿院里长大),也不牺牲抚养孩子所带来的满足感。这种似乎不是一个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
[4] 斯图尔特-拉歇尔(Rachels,2014)只考虑了彼得-辛格论点中的这一种 anti-natalist 的暗示。 他一般把自己的论点称为「反对生孩子的饥荒救济论证」(Famine Relief Argument against Having Children),但他简要地指出,这一论证满足的是机会成本的诉求。他没有讨论彼得-辛格的论点和 anti-natalism 之间的其他联系,我将在本文中介绍这些联系。他的论文和我的论文之间也有其他区别。例如,他考虑了一些我没有讨论的反对意见(因为我认为它们对我的目的不够重要),而我考虑了他没有考虑的反对意见。即使在我们讨论相同的反对意见时,我们也常常采用不同的方式。我不会在这里讨论所有这些差异,因为它们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彼得-辛格论点中不同的 anti-natalist 含义,而不是讨论斯图尔特-拉歇尔对这些含义之一的表述。然而,有效的利他主义者,包括彼得-辛格(2015)和其他同意我们对世界上的穷人有广泛义务的人,可能会被迫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花在养育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身上的资源,反而可以用来拯救更多的人免受比在(人道的)孤儿院长大更糟糕的邪恶。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不仅仅是遗传的后代,还有养育孩子的满足感。然而,如果我们以彼得-辛格理解的苛刻方式接受他的结论,我们可能会被迫同意,即使是这种牺牲的道德重要性也无法与我们由此可以防止的坏事相比。
然而,有效利他主义者,包括彼得-辛格(2015)等同意我们对世界上的穷人有广泛的责任的人,可能会被迫得出结论:一个人花在养育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身上的资源,也能用来拯救更多的人免受比在(人道的)孤儿院长大更糟糕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不仅是遗传性的后代,还有养育孩子的满足感。然而,如果我们以彼得-辛格所理解的苛求方式来接受他的结论,我们可能会被迫同意:即使是这种牺牲的道德重要性也无法与我们由此可以预防的坏事相比。
这并不是要否认其他人可以将这些情况视为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可能会争辩说,放弃抚养孩子,至少对许多人来说,会威胁到他们的人类繁荣,从而构成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牺牲。[5] 然而,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可以把作出更多牺牲的道德重要性与防止极端贫困相提并论,他们对彼得-辛格论证结论的理解会比其论点的苛求度低很多。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只是一例。任何认为放弃创造亲生子女或抚养亲生或非亲生子女所构成的牺牲是有可比性的道德意义的人,都可能认同一个比彼得-辛格得出的结论要求低得多的结论。因为如果放弃创造和抚养孩子是一种有可比性的牺牲,那么其他许多牺牲也很可能有可比性。这是因为养育孩子并不是唯一代价高昂的个人项目,它对人们来说可能意义重大。[6]
综上所述,彼得-辛格的论点似乎使他承诺于以下几点。
如果我们能够防止坏事发生,而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就应该这样做。2. 极端贫困是坏事。
我们可以在不牺牲任何有可比性的道德意义的情况下,防止一些极端贫困的发生(通过拒绝生产儿童并重新分配这些资源)。
因此,我们应该防止一些极端的贫困(通过停止生产儿童和重新分配资源)。
彼得-辛格自己也想避免这一特殊的 anti-natalist 结论。他是通过拒绝他论点中第三点的运用来避免的。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发达国家的个体生孩子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知道这将使他们更加偏心,对整体利益的贡献更少」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他更担心「如果那些为他人着想,行为利他的人决定不生孩子,而那些不关心他人的人继续生孩子,未来就不会好了」(Singer, 2016)。
[5] 有几个人在阅读本文的草稿或听我介绍本文的论点时,提出了这种反对意见。
[6] 我在下文作出解释。
换句话说,他认为停止生育会涉及到一个具有相当道德意义的牺牲。当彼得-辛格提及「具有可比性的牺牲」时,他指的不仅是某人为了防止坏事发生而放弃的某种个人的东西。他指的还有坏事被阻止后可能会失去的其他的好事。[7]
然而,除非他认为利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影响(即便不是由基因所决定),否则他的回答并非是生育的一种辩护。如果利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后天的,而不是天生的,那么父母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授给被收养的孩子。那些接受彼得-辛格结论的人,可以在不牺牲未来利他主义的既定利益的情况下,阻止被遗弃的孩子在孤儿院中(包括贫困的第三世界孤儿院)成长。[8]
自然界所起的作用可能足以使没有利他主义遗传倾向的儿童极难变成利他主义者。然而,即使有这种可能性也不足以为一对富裕的夫妇决定生育的行为提供辩护。首先,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目前不知道基因在产生利他主义个性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其次,还有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即使基因对利他主义有重大影响,一个人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遗传不到这些基因,而一个人收养的孩子也有可能从他或她的亲生父母那里得到这种基因。
也许一个利他主义者自己的亲生孩子没有得到利他主义基因的机会比收养的孩子有利他主义基因的机会要小。然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必须与以下的确定性相权衡:一个人花在自己创造的孩子身上的钱将不能用于已经存在的孩子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某种确定的利益因为一个仅仅是推测的利益而被放弃了。就算推测的利益被证明是真的,仍然有一个问题,即这种利益是否比短期利益更大。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9] 因此,至少需要对未来可能的利益打上一个折扣率,其结果是这些利益不太可能超过放弃生育和用本来用于抚养孩子的钱来帮助他人的利益。
对于机会成本的论证并不能使彼得-辛格承诺于极端的 anti-natalist 立场——即创造孩子总是(甚至几乎总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灭绝不能成为「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如果所有的富人都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贡献——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做出贡献——那么全球贫困就能在不需要任何人放弃创造和抚养孩子的情况下被防止。然而,彼得-辛格认为,一个人自身责任的大小部分取决于其他人是否确实履行了他们的责任。苛求的结论之所以会产生,是当他人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机会成本论证表明,根据辛格的各种承诺,苛求的结论应该扩展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放弃生育,也可能包括放弃养育收养的孩子。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富裕的辛格主义者应该拒绝生育。
[7] 这点既能从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看出,也可以从他在其他地方的解释中看出,他所说的「在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是指「在不引起其他有可比性的坏事发生,或做一些本身就错误的事,或未能促进一些道德上的好事的情况下,在重要性上与我们可以防止的坏事相当」(Singer, 1972, 第 231 页)。
[8] 只有当被遗弃需要领养的孩子存在的情况下这才成立,但这种情况无法消减在那之前考虑它的动机。人们现在(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可以养育具备利他性格的孩子,并不需要首先进行繁殖。
[9] 彼得-辛格(据我所知)并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他曾回答过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在捐赠好,还是先投资后捐赠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说,如果一个人有巴菲特那样的投资技能,那么他就应该先投资,后捐赠。否则,他不确定这么做是好的。他引用了克劳德-罗森伯格(Claude Rosenberg)的观点:「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增长速度是『指数级的』,大于资本回报率」,但他指出这「很难证明或反证」(Singer, 2009, pp.37-38)。
[10] 更广泛地说,他认为我们的职责受到他人正在做和没有做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如果接受利他主义者不生育,那未来的利他主义者就会减少,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对利他主义夫妇都可以用这一点作为自己生育的理由。其他利他主义者的生育越多,某对利他主义夫妇就越不能以需要新一代的利他主义者来为自己的生育辩护。当其他人在为未来的利他主义者提供更站不住脚的利益时,这对夫妇反而可以提供立即的且更可靠的利益。